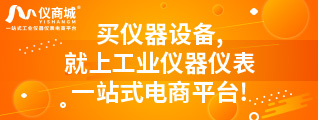近期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,会议通过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,要求瞄准全球科技前沿,聚焦产业升级、民生改善、生态治理等重大需求,强化资源集成和协同创新,动员社会资本等各方力量参与,加快推进集成电路等重大专项。此外,李克强还指出要开展5G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,推动信息技术更好服务经济升级和民生改善。那么,5G通信技术还存在哪些问题,在产业扶持中政府又应该注意什么呢?
5G标准最后胜出者还待揭晓
在2014年,国内刚刚用上4G,不久后,5G通信又映入人们眼帘,5G通信顾名思义是第五代通信技术,具有连续广域覆盖、热点高容量、低功耗大连接、低时延高可靠四大特点。
连续广域覆盖能够实现在偏远山区、地下车库、高速移动状态下,以保证用户的移动性和业务连续性为目标,为用户提供100Mbps以上的高速业务体验。

热点高容量指的是在人口密集区为用户提供1Gbps用户体验速率和10Gbps峰值速率;在流量热点区域,可实现每平方公里数十Tbps的流量密度。
低功耗大连接能保证终端的超低功耗和超低成本的前提下,面向智慧城市、环境监测、智能农业、森林防火等以传感和数据采集为目标的应用场景,提供具备超千亿网络连接的支持能力,满足100万/km2连接数密度指标要求。
低时延高可靠主要面向车联网、工业控制等垂直行业的特殊应用需求,为用户提供毫秒级的端到端时延和接近100%的业务可靠性保证。
不久前,中国华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(极化码)方案,成为5G控制信道eMBB场景编码方案。消息一出,在网络上就炸开了锅,甚至有媒体用“华为碾压高通,拿下5G时代”来形容这次胜利。然而媒体这种报道既不符合客观实际,也有把eMBB场景短码的控制信道的标准制定权等同于5G标准的嫌疑。
实际上,核心专利是由几个体系来组成的,高通在3G时代掌握拥有软切换和功率控制两大核心专利以及两千项外围专利,才具备了征收“高通税”的技术资本。要想在5G时代拥有一定话语权,仅有eMBB场景编码方案短码控制信道的标准制定权是远远不够的,必须在多址技术、多天线技术、射频调制解调、软频率复用、编码等方面都要有一定话语权。
据业内人士分析,“现在要实现蓝图中所设想的5G,在技术上是有一定困难的,而且也没有特别大的技术突破……现在一些比较流行的5G技术,有的是一些假的技术,或者是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技术,有的技术在实验室能够实现,但商用起来就存在很大的问题……这是目前5G技术上一个普遍的现状……出现假的技术这并不奇怪,做研究的人为了分政府的拨款,总会找一些名目来套钱,就必须编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,而企业和科研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,也会把一些垃圾专利想方设法往标准专利里塞……在研究中难免选错技术发展方向,比如现在多址NONA这个技术,从理论上证明这个大的方向是存在问题的,但几乎所有公司在这方面投入了大把大把的财力和人力,已经到骑虎难下的地步……”也正是因此,有观点认为,现在所谓的5G其实是4.5G。
在发展规划上,国际电联的计划是2015年将完成5G国际标准前期研究,2016年将开展5G技术性能需求和评估方法研究,2017年年底将启动5G候选方案征集,2020年年底完成标准制定。而根据工信部、中国IMT-2020(5G)推进组的工作部署以及三大运营商的5G商用计划,中国将于2017年展开5G网络第二阶段测试,2018年进行大规模试验组网,并在此基础上于2019年启动5G网络建设,最快到2020年启动5G商用网络。
在技术研发上,国内整合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、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、华为、中兴、大唐等公司和科研机构携手开发5G通信技术,而在最近一次eMBB场景编码方案的争夺中,来自海峡两岸的华为、中兴、大唐、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联想、小米、VIVO、OPPO、酷派、阿里巴巴、展讯、中国移动研究院、信威通信、宏碁、联发科、台湾国立大学等公司、科研机构全部集体抱团,这背后未必没有中国政府的组织协调的因素。至于中国通信产业能在5G时代处于怎样的地位,在很多技术尚且不成熟,或者存在一些障碍的情况下,现在就言之凿凿5G标准花落谁家,未免过于草率。
政府在产业扶持的角色
目前,产业政策执行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,比如政府过多的介入实际上并不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。产业界人士也曾向笔者表示,政府应更多的是一个规则制定者,并把控宏观的发展方向,最好不要去做具体的执行者。因为一个课题或者科研项目如果是政府主导的话,由于各种政商关系和一些官僚尸位素餐,就很容易演变成大家一起忽悠政府的钱,拿到钱了之后各回各家,黑一点的不了了之,厚道一点的最后做出一个只能看看,但用不起来的技术成果。
政府在给政策的过程中,对于扶持对象到底是国外巨头的马甲公司还是真自主公司,以及技术实力和市场前景如何并不是特别具有甄别能力,能拿到怎样的扶持力度和项目,背景和政商关系才是关键中的关键,因此,政府过多介入的话,会导致资金利用效率有限,而且好钢用不到刀刃上。
另外,政府扶持中也存在一个拉偏架的问题——政府很喜欢看谁弱一点,或者不行了,就去扶它一把,看谁能自主发展了就不管了,只去帮弱的,而且帮助力度还非常大,发展得好的公司靠自己努力取得的优势一下子就被行政力量抹平了,这对能摆脱政府扶持、能自主发展的公司非常不公平,搞得竞争法则不起作用了。
如果是政府制定规则,具体执行由企业来主导的话,比如搜狗资助清华大学做人工智能,因为企业是追求经济利益的,也是懂行的不会被忽悠,大家就会想着把这些钱做出什么成果,而且只要做出技术成果,企业可以拉来客户,可以摆脱技术突破但只能躺在实验室、无法被商业化的困境。
大基金帮扶模式讲究科学配置
截至2016年10月,首期募资规模1387.2亿人民币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项目40个,企业28家,承诺投资额也已接近700亿元,已投项目带动的社会融资超过了1500亿元,其中,IC设计占总投资的27%,晶圆制造占总投资的60%,设备制造占总投资的2%,封装测试占总投资的8%。
在业绩上,虽然28家企业2016年增幅略微下降,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,紫光集团、三安光电等成为大基金投资的重要受益者,长电科技在国家扶持下收购了新加坡星科金朋,一举迈入全球前10封测公司,中芯国际在获得大基金投资后扩建工厂。不过,从资金的投入到企业技术突破和商业上的成功有一个时间周期,具体的成效会在几年后慢慢体现出来。
总体来说,相对应补贴送钱的方式,国家产业基金扶持方式对于扶持产业做大做强,资金的利用效率会更高,成效也会更好。
不具优势的行业如何适者生存
不过,如果只有这种对龙头企业的天量资金投资扶持的话,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只能成长为瘸腿的巨人——因为很多行业里,中国大陆目前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龙头企业,只有在国外巨头倾轧下勉强生存的一些小公司。
比如,比如IC设计中的CPU、GPU、DSP、FPGA,以及用于辅助设计的EDA工具等等。国家产业基金因为是拿国家的钱在投资,保值增值是必不可少的,因此不可能去做风险较大的投资,只会投资一些已经有一定规模,前景较好的企业。换言之,国家产业基金只能锦上添花,无法雪中送炭。
而且站在那些小公司的角度,由于自身的体量太小,如果拿股权换资金,拿少了没意义,拿多了也就意味着大基金控股,失去公司控制权,在本来就被国外巨头打压的情况下,被大基金控股后难免导致外行领导内行,很有可能会把这些本来就生存不易的小公司带到坑里。
因此,很多绝对劣势的领域,国家产业基金现行的做法是无能为力的,而过去那种直接给钱的做法既不科学,效果也不好。相比之下,给出生存空间的做法不失为解决之道——划出一块保留地让国内自己设计的CPU、GPU、FPGA等芯片可以被用起来,比如把党政军市场拿出来,把这块封闭市场给予国内公司去生存和竞争,谁的产品好,不能只听领导和专家的意见,必须倾听用户单位的声音,再以政府择优采购的方式给做得好的公司变相给予资金扶持,并且在实践中使用自主设计的芯片,在使用中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,实现技术的螺旋式上升,并在使用中慢慢构筑起软件生态,最终实现自主技术的成长和国内公司逐渐成长壮大。
如何构建产业健康发展模式,不管是对通信、集成电路、仪器仪表产业,都显得尤为重要,政府在这部分的引导和扶持很关键。